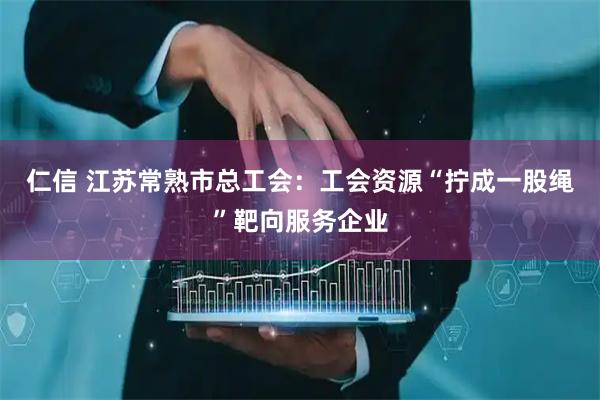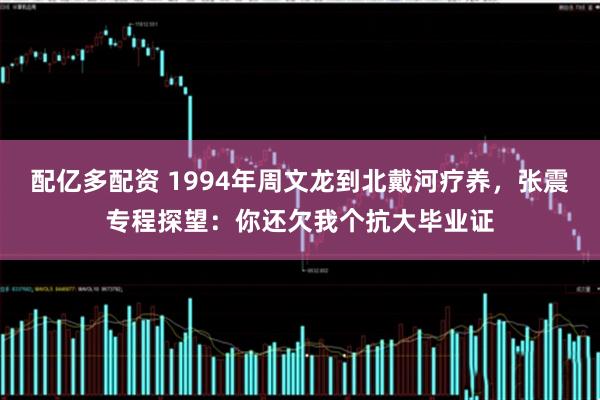
“老周配亿多配资,九年前跟你说的那张毕业证,今天带来了没有?”——1994年8月12日北戴河疗养院走廊里,张震一开口,湖南乡音浓得像刚出锅的糍粑,周文龙笑得前仰后合:“副主席,您可真不嫌旧话长!”

那晚两位八十多岁的老兵一壶铁观音喝到微亮,卫生员顶着黑眼圈守在门口。外人只听得“龙岗”“草地”“饷银”这些零散词,真正的内容却是半个世纪的刀光血影。张震要的那张毕业证,来源于三十七年前的一段“小插曲”,而这段插曲又牵出周文龙一生绕不开的“后勤”二字。
周文龙1909年生在浏阳,家里小有薄田,父亲会烧石灰,辛苦但不穷,典型的小康农户。周家舍得投资教育,少年周文龙从高小一直读到长沙大麓中学,反帝爱国的火苗就在课堂外被点燃。1929年他加入农协,次年扛枪进红军。那时识字的战士稀罕得很,他递补到三军团五师当书记官,毛笔字写得漂亮,一头扎进档案堆,却没躲过血与火。

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期间,他在广昌阵地换了足足三次绷带,仍然扛着掷弹筒往上冲;浑身带血回到医所,只挤出一句话——“山头保住了”。养伤未愈,长征号角响起,他拄着木棍赶回部队。过草地时痢疾差点要命,彭雪枫扶着他说:“挺住,出了草地再倒下也值。”周文龙就这么被两名警卫拖到班佑,命悬一线却没掉队。
1936年夏,他被选送红军大学一期深造,年底留校管后勤。1937年2月,张震提着被褥来报到,俩人一个管学杂费一个埋头听课,不料卢沟桥枪响配亿多配资,张震火速奔前线,临行笑着嚷:“周副部长,等我凯旋回来补张毕业证!”证件就此成了半个世纪的“口头债”。

进入抗战,周文龙的舞台从教室换成仓库和银库。1940年春,他奉命随朱德赴西安讨要被扣军饷。走到陵川,他先把50名被囚兵站人员要了出来;到了洛阳,又从卫立煌的特务营“领回”46名干部。有人打趣:“周副部长,您是押饷官还是押解官?”他只抖抖肩:“欠账得有人收,对不对?”
最惊险的是进西安第三天,出纳员吴福兴被特务绑走。周文龙接到求救纸条,先给送信的新兵两块银元,又打电话痛斥警备司令部。对方嘴上说“误会”,却拖到第二天才松口。为了防止再出岔,他规定:所有携款人员,出门必须双人同行、路线当晚汇报。正是这些看似繁琐的细节,让6月29日那批拖欠八个月的饷银完整送回前线。

有人只记得他是冀南银行副董事长,却忽略了另一顶帽子——“搬运部长”。1942年日军围困太行,周文龙带八条驴拖着600万冀南币硬闯封锁线。驴子被炸死,钱袋没人抬,他命令把纸币散埋山沟石下,标出暗记,三昼夜苦战后原数追回。战士打趣说:“这比押镖还刺激。”他淡淡回一句:“后勤要的就是不失一分一毫。”
再往后,中原突围、淮海会战、渡江作战,每一次大兵团行动都少不了周文龙的背影。华北军区与总后勤部成立初期,仓库里旧弹壳堆成山,新出厂炮弹却寥寥。他掰着指头给杨立三算账:“前线一天就耗几百吨,我们得逼着工厂三班倒,还得翻修缴获弹。”抗美援朝时,1.4万吨弹药需求摆在桌面,全国月产才1500吨,他硬是把旧日制式炮弹统统翻新,凑齐第一批急需;与此同时,天津、石家庄女工连夜缝出十几万套冬服,炒面从各地火车皮运上前线。志愿军司令部回电:二十六个字——“供应及时,部队无后顾之忧,敬礼!”

1955年,他正式离开军队转赴石油工业部。黄克诚送行时只说一句:“那里也缺后勤,你去正合适。”周文龙点头接令,没再回头。他懂,换了战场,原则没变——保障,还是保障。
时光回到北戴河。张震提起毕业证,是玩笑也是敬意。因为他清楚,若没有周文龙这类“隐身人”撑起粮弹、药棉、盐巴、军饷,再漂亮的战术都会半途折翼。周文龙把茶杯举到胸口,声音低但清晰:“老张,你的毕业证一直在我心里,真正要还的,是战友、是烈士、是那些把生命留在后方线上的年轻面孔。”

走廊尽头,海浪声翻滚而来,黄昏中的老兵一言不发,相视而笑。毕业证兑现不了,但一纸文凭又算什么?他们彼此都明白:真正的“证书”,写在新中国的土地上,盖章的是胜利。
铭创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